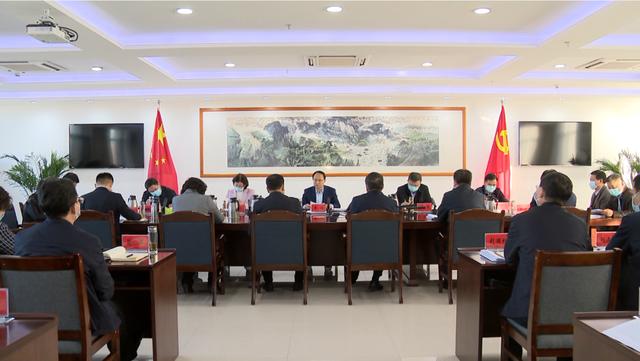刘炜
新陂头河直通茅洲河,算是茅洲河的分支。如果说茅洲河是一棵大树,新陂头河就是它伸出去的树枝,新陂头村就是它的果子。
新陂头村,据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,那些褐色的小瓦,分泌岁月的红与黑,现在已被太阳晒干,不管今后还有多少风雨,它们都是深褐色的了。那些褐色的小瓦,就像是一群麻雀,落到了这里,就不再飞走了。在清晨,我听到的鸟鸣,时而稀疏时而密集,却始终不见鸟影。或许,那些鸟呜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瓦发出的啁啾。不信,你伸手去摸,还能摸到六百多年前南宋腹部的余温。新陂头村的褐色小瓦姓梁,也姓陈,它们啁啾的声音,几乎都在百家姓的音韵里,都是大姓。
茅洲河是新陂头河的根源,它涨水,新陂头河涨水,它落水,新陂头河也落水,就像一颗心脏的右心室与左心室,右跳一下,左也会跟着跳一下。
新陂头村的旧民居,矮小低调,好像六百多年的时光,对于它就只是些平凡而又普通的日子,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。它们被现代高大的建筑包围,也并没觉得不安,它们享受着岁月的静好。
陂头,据说是指筑在大小河道上拦河蓄水的水利设施,是祖先留下的古老水利工程。谁也说不清一条河上那些大小陂头的历史,仿佛有了河就有了陂头。导游说,新陂头村的制高点在一幢农家楼的天台上,它可以鸟瞰全村矮小的过去,也可以远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高大的教学楼,和新陂头村更美好的未来。这岁月的不等式,并不曾让我觉得突兀,反而有了舒缓的张力与过渡。
这幢楼的主人在香港经商,平时很少回家,因此我们能登上新陂头村的制高点拍照、写生、眺望,是一种幸运。我站在天台上从高处往下拍了旧时光里的小瓦,也拍了阳光下的脚手架。晴朗的天空,蓝天与白云构成的向往,有人说有点像新陂头村奶牛场的花斑奶牛。
新陂头村有制高点,也没有制高点。它还没有停止生长,还没有停止在时间里向前奔跑,还在奋力地向更高处飞翔。所以,无论我站到多高的楼顶,新陂头村的明天一定都会比我更高,比我看到的和眺望的更高。
新陂头河是茅洲河的支流,它曾灌溉过千万亩水稻,千万亩甘蔗。而现在它像个老人,独自在这里安静地躺着,晒着冬日的阳光,慈善而又安详。有那么一瞬,我闭着眼睛看见新陂头河的河水,被抽水机抽到了渠道,月光下环绕着稻田欢唱,那稻花的香呵,扑面而来。那甘蔗的甜呵,沁人心脾。农耕时代的茅洲河哺育了茅洲河两岸的所有生命,新陂头河就是它搂着新陂头村的一只有力而又温暖的臂膀。我爱新陂头河的前世,也爱新陂头河的今生,更爱新陂头村美好的明天。
在新陂头村,我一直跟在导游与一群摄影师的身后,几乎是寸步不离,生怕在新陂头村的小巷里迷路,走错了方向,穿越到南宋,再也走不出来。
我们在新陂头村还遇见了一堵断墙,据说是发洪水时冲塌的,是新陂头河借助了茅洲河的力量将它冲塌的。也许每一件事物都有善的一面与恶的一面,包括河流、动物和人。
那堵墙之所以至今还未全部倒塌,是因为有一棵倔强的榕树用自己的根须保护着它,它翡翠般的绿叶,在十二月,想告诉我点什么?是新陂头村的历史,茅洲河与新陂头河的故事,还是新陂头村从南宋到现在的六百多年间,新陂头人艰辛的劳动与梦想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断墙旁边曾经香火旺盛的寺庙早已消失,只剩下一个遗址,被岁月留了下来。就像寺庙里的木鱼声至今还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挣扎,香火还在燃烧延续,他们相信他们双手合十的祈祷,还会得到神的回应。
洪水留下的水位线已经模糊,墙上的青苔也已被太阳晒干。只有在雨季青苔才会返绿,好像落在新陂头村的雨,来自六百多年前的南宋,来探望了一下新陂头村。
如果人生有轮回,百年之后我们也可回新陂头村探望我们自己,在新陂头村走街串巷的身影,再相约去小酒馆痛饮一场,诉说一下彼此的见闻与思念。
当我走出古村落,就好像一下子跨过了新陂头村六百多年的历史,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,村里的道路上新鲜的斑马线,让我又返回了二十一世纪,返回了原本的生活。